江淹至爱的浦城“醉灵芽”
早年回故乡时,母亲都会从小瓦罐里掏出一撮茶,冲泡给我喝,说是为我洗尘解困,丰神益思。不过,母亲称茶为“瞧米”,我一直以为是她的乡土话。
“故乡云雾茶清香,喝多了会醉人的哟。”去年夏初在老家,茶农福邦请我去品泉山茶,一盅又一盅,酒醉身倒,茶醉人醒,贪杯的我夜难寐,灯下翻开林治先生所著的《神州问茶》,书由中国茶学泰斗张天福先生鼎力推荐,在“问茶史”中赫然写着:根据对武夷茶最早的文字记载,南北朝时期“梦笔生花”的一代文豪江淹在浦城当县令时,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:“武夷山脉所产之珍木灵芽皆淹平生所爱。”文中珍木灵芽”即指茶叶……
原来浦城也是茶的故乡,我如梦初醒,欣喜若狂。但翻开《八闽古邑浦城》一书,“人物春秋”江淹《自序》中说:“爱有碧水丹山,珍木灵草。”究竟是灵草,还是灵芽?或二者合一?莫是当今大茶师的牵强附会?生于斯长于斯的我,竟找不到江淹饮茶之说。
茶字究竟何义?疑问重重的我在《茶酒论》寻得答案:“百草之首,万木之花,贵之取蕊,重之取芽。呼之茗草,号之作茶。”《茶疏》也描述:“天下灵山,必产灵草”。再读《神农本草》称茶为“荼草”,有“神农解毒,尝百草发乎茶”之说。
茶,唐兴宋盛,唐代陆羽《茶经》里名有“荼、清、茗、茶等十多种,都是“草”字头。于是,茶圣在写《茶经》时,将“荼”字减少一划,改写为“茶”。遗幸,他没入闽,未尝过武夷山茶,只说南方有“佳木”。 中国的道家历来也把茶叶视作“灵芝草”。清代蒋周南茶诗中就有“谁信芳根枯北苑,别饶灵草产东和”之句。看来,“灵草”,即是“灵芽”,都是茶的本义,江淹的碧水丹山当指武夷山脉。
故乡的醉灵芽,竟茶醉千年鲜人知,如释重负的我,仿佛在醉梦中,走上当年的浙闽通关的泉山古驿道,看见中州大才子江淹黜谪入闽当县令来了。一路风霜,他脸色神殇,容颜憔悴,走过苏州岭,歇脚忠信小山村,村民得知新县令路过,争以煮“芽草”热汁献上。江淹饮后,疲惫即无,精神振奋,惊叹是何“醒脑玉液”?
村民指房前一株常绿灌木告之,此芽叶十分珍贵,摘下晾干贮藏时可作药草用,亦可煮之作饮汤喝。于是,“碧水丹山,珍木灵草”成了他的“平生所至爱”。
江淹到南浦后,政清民仰。闲时,他游山玩水,访仙问道,寄托离朝思想向往。追踪古人脚迹,我们到梦笔山等觉寺品茶,寻找山脚下那几块奇石——神人赠送江淹的五彩笔、纸、砚、墨的文房四宝。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传说,一天,江淹漫步莲塘这座小孤山,徜徉奇景,流连忘返,夜宿山上,睡梦中见神人郭璞授他一枝五色笔。江淹问及邑中“珍木灵芽”时,郭璞笑道:“今君见《尔雅·释木》,今呼早采者为茶,晚取者为茗,一名瞧。”梦笔生花,灵芽健体。江大才子,梦获二宝,人爽情愉,一手挥彩毫,一手把茶盅,连连赞曰:乃真“醉灵芽”也。
传说神奇,且神秘。查阅南朝宋山谦的《吴兴记》,历史上果真有着称“瞧”为茶的载记。遗幸的是江淹在南浦任职三年,时间短,几次想游武夷山,但终未去,只知那里亦有“珍木灵芽” 。
从此,江淹文思大进,灵感日新,他在《渡泉桥出诸山之顶》中描述:“万壑共驰骛,百谷争往来。行行讵半景,余马以长怀。”其词采艳丽,峭拔苍劲,精切和谐,抒情扬怀,盛扬南朝文风。
呵,江淹“梦笔生花”,是古邑的丹山碧水,醉甜了你创作源泉,是山城的“灵芽茶米”,醉红了你神笔文章!然而,一方山水养一方人,你去京城虽连连官升,那里却没有你的亲水丹岩,也没有你醉人的灵芽茶,怎么不“江郎才尽”呢?
南朝越千年,灵芽使人醉。自江淹后,又有多少诗陶醉在碧水丹山的一片片灵芽中。白居易说“绿芽十片火前春,应缘我是别茶人”。元稹道“茶,香叶,嫩芽, 慕诗客,爱僧家”。曾巩颂“一杯永日醒双眼,草木英华信有神。”欧阳修赞“乃知此为最灵物,独得天地之英华。”闵龄称“啜罢灵芽第一春,代毛洗髓见元神”。林锡翁誉“百草逢春未敢花,御花葆蕾拾琼芽”……闽北大儒理学家朱熹也有一首著名的《咏武夷茶》诗句:“采取灵芽余自栽,红裳似欲留人醉”。
“家家茶酒供佳客,处处香花祝有年。”如今走在故乡,人们在梦盼千古茗枞“醉灵芽”,醉香昨天的古邑,醉美明天的山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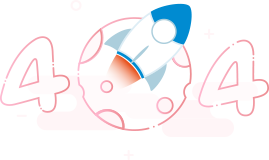
 故乡记忆之父亲的手
故乡记忆之父亲的手 茶园里的母亲
茶园里的母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