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过喝茶的岁月
在不惑之年的岁月里,工作生活压力大,我们是单亲家庭,儿子还小,要顾及生存还要教育儿子的成长。所有的困难和压力都要自己扛。我几乎嗜茶如命,我爱茶,对其产生了深深的敬意!它伴随着我走过多少孤寂无助的岁月,说来也怪,茶竟使我从柔弱者变得坚强起来。
小时候,父亲被划为右派,离开大学发配到陕南一家煤矿当井下矿工。母亲随父亲到偏远的陕南当山村女教师。我自然就被外婆收留了。
外婆特爱喝茶,清晨起床第一件事,先在炉子上蹲一壶水,然后再去洗涮清扫卫生。壶水沸腾了,外婆抓一把茶叶丢进一个大瓷壶里,冲上水,盖好盖,捂上数分钟,然后她用一个不大而精致的紫砂茶壶———这小壶也许是姥爷给外婆留下的念想(姥爷当年在台儿庄抗敌牺牲)。只见外婆娴熟地从大瓷壶里倒入泡好的浓酽的茶汤进小紫砂壶里。外婆总是双手捧着小茶壶,然后有滋有味的吮吸着壶嘴。她边吧咂嘴边哈着气,从厨房走进里屋,从里屋走进外屋,再走出小院,久久地站在院坎旁边凝神望远,一年复一年,远眺着绿色或金黄色的庄稼地,一小口一小口地呷吸着苦涩浓洌的茶汁……嘴里时不时还发出喃喃的自语……她是在操心牵挂她的儿女们。那时,老姨支边在新疆的伊犁,爸妈在深山里的煤矿……她是在凝神远望在外面受苦受难的儿女们,是在牵挂她二十二岁就开始守寡养育的儿女们。
记得是小学三年级那年,父亲回家来接走了我,他对外婆说:他已被摘掉右派的帽子,现在是煤矿工会里的文化教员,他采访搜集煤矿的矿史,用漫画的形式做成图片展览,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,矿党委表扬了他,于是激发了他更高的创作热情。他熬更守夜地又编写了以矿史为题材的剧本《煤山血泪》。这次接我去是要去顶演一个穷孩子的戏角。我一听乐坏了!蹦的八丈高!而外婆却因舍不得我的离开,吧嗒吧嗒地掉眼泪……
于是,少年时期,我是和母亲还有两个弟弟在学校长大的。母亲每天除了上课以外,还要顾及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活,衣食住行、缝补浆洗,她哪样都得操心。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时期,要想让孩子吃饱肚子不容易。母亲绞尽脑汁给我们瓜菜代,用南瓜、土豆、红薯、野菜糊弄着我们饥饿的肚子。每到夜晚,母亲都要用一个父亲煤矿发给井下工人的大磁茶缸,抓一把山里的大脚片茶叶,浓浓地泡一茶缸酽茶,然后有滋有味地要喝上十来分钟。只有那个时候,我才能看见母亲脸上有一抹红云绽放,露出恬淡的笑容。喝着山里的粗片茶,也许是她那个时候的最大人生享受!我看见母亲桌子上垒着像小山一样高的几大堆作业,待她批改完作业还要为儿女们洗衣缝补,备明日的吃食……我常常在那样的夜晚睡醒一觉后,看到母亲还在忙,她秀丽端庄的脸上,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。
每当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挫折和苦难时,我便喜欢躲在家里静静地一人呆着,默默地舔自己的伤口……这时候,必有一杯浓酽而苦涩的茶陪伴着我,体贴入微地滋润着我孤单无助的心灵。它陪伴着我长好伤口,珍惜人生,咬咬牙,更坚强地活着!
儿子大学毕业,工作分配在杭州,那真是个美丽的地方。知母莫若儿呀!儿子自食其力会挣钱以后,第一次送给我的礼物便是:浙江的狮峰龙井。那是我五十岁的生日接到的最珍贵的礼物,还有一大捧鲜花……儿子的生日礼物长久的温暖着我孤独的心房和平淡的日子。
每天下班后,尤其在忙碌了一天,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时,我常常不感到饥饿,不急于想吃饭,更想喝茶。
福建乌龙茶、铁观音皆属佳茗,其琥珀色的茶汤入口,清香甘冽,留在舌尖的茶韵散布四肢百骸,通体舒泰,消除疲劳;六安瓜片、云南普洱,甚至陕南的胶股蓝各有所长。
但我以为唯独浙江的狮峰龙井最妙。茶盅的边缘浮绕着翠碧的氤氲,清亮鲜嫩的叶片透出一种近乎乳香的茶韵……这种特别的感觉也可能更源于对儿子至爱的特殊感情。
我不喜欢红茶。我嫌它太像浓酽的酒了。也拒绝花茶。因为它的香是外加的,是别的花的香,就像是一个被脂粉搽香的女人,香是香的,香得刺鼻,却无一点女人自身的气息了。我本人一向素面朝天,从不涂脂抹粉。我崇尚本色自然。
我只饮绿茶,一因为它的绿,绿是茶的本色;二因为它的苦,苦是茶的真味。是绿茶沏出的一壶苦,同时又是苦茶沏出的一壶绿。这茶却又是清淡的,是清淡的绿与清淡的苦的混合。
喝茶,由浓到淡,由苦到甘,然后就慢慢的去品淡淡的甘甜,人生亦如此。悲欢离合都经历过的我,现在逐渐走向淡定和从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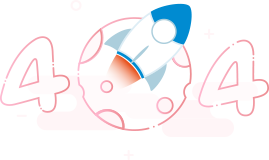
 故乡记忆之父亲的手
故乡记忆之父亲的手 茶园里的母亲
茶园里的母亲